2017年,德国科研人员在研究了9岁-21岁的ADHD(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人士后发现,对负面社交暗示更敏感的人,患抑郁的比例也更高。
在知道自己既不善社交,也缺乏资源甚至意识来提高自己的社交能力后,我感到和世界格格不入。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家,我都渐渐习惯了躲在为自己挖的坑里,在里面,我可以退回到我的内心世界—这就是我拥有的一切了。
我既不懂数学,也不懂青春期女孩间的政治,于是我把注意力集中在了我能控制的事情上:我的外貌。我们想要吸引的男孩和整个文化都在传达一个信息:女孩要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完美。我不知道我在人生中最脆弱、最在意形象的阶段被要求打扮成男孩,是否促使我对自身外貌的审视变本加厉,但是似乎我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做得越差,我对自己外表的批判就会变得越发尖锐、迅速、大胆。
平心而论,我的身体槽点满满:眼睛太大,腿太瘦。可我对此无能为力,于是我把改造重点放在了我身上所有的毛发上,包括我浓密的眉毛和后颈的汗毛。我确信我后颈的汗毛比别人往下长得更多。我的“小胡子”比大多数同龄男孩都要早长出来。“上唇毛”,我妈这样叫它,但无论什么字眼都无法让我接受它。我很讨厌自己的身体,我也觉得如果我外表的意大利族群特征不那么明显,我可能少讨厌自己一点。我觉得只有我抹掉一切与我童年相关的印记,才能融入周围的少男少女。那个意大利小女孩/小男孩必须消失。
为此,我每周都要在浴室里当一回少年化学家。一份活化剂,两份乳膏,用小铲子搅啊搅,搅拌成糊,然后涂在身体各处:手臂、腹部、脸上、后腰(这是穿当时流行的低腰牛仔裤时最显眼的部位)。漂白剂让我皮肤灼热、刺痛,疼得我在米色的小浴室里蹦来蹦去,但为了确保我所有的黑色体毛都变成看不见的柔软金色绒毛,我硬是让这种混合物留在皮肤上的时间比建议时间长一倍。越是不舒服,我就越兴奋。等我在淋浴下把它洗掉,我的皮肤已经被漂白剂弄得红一块肿一块,但看着半小时前还是黑色的体毛变成了金色,我还是笑了。
有一次,我偷偷溜进我妈开在地下室的家庭美容院,把滚烫的蜡涂在后脖颈,想要去掉那里的汗毛。结果当然是被烫伤了,伤疤看起来就像一个尴尬的大吻痕。这么看还是漂白剂更安全,所以我后来一直用漂白剂。
接下来我开始淡化眉毛。这在当时并不是一种潮流,但我就是想让眉毛消失,这样我就能得到我的“真身”:一个天然的金发女郎。我的眉毛确实变成了金色,但在阳光的照射下,它们呈现出明显的橙色调,就像两条金色的毛毛虫粘在我脸上,我因此受到不少嘲笑。
再接下来是我的头发。尽管我对很多事情束手无策,对别人对我的各种看法深信不疑,比如我在学校是个差生,在家里是只懒虫,我自己对自己的看法也很偏颇,但我还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能给我带来即时满足的事情上。
把头发漂成金色比重塑内心的情绪抓手要容易得多,但任何一个发型师都会告诉你,在自家浴室用盒装染发剂把头发染深或染浅超过三个色阶是有风险的。但这就是染发的意义所在啊。我去了两次商店,消耗了三盒金发染发剂,终于化险为夷,喜提金发。然后,我把眉毛拔成了两条短横线。当我从小小的浴室里走出来,简直是低配版的格温·斯蒂芬妮。
我真正想成为的人是科特妮·洛芙。她唱“我假装得那么真,已经超越了假装”(“Doll Parts”)时,俨然就是在说我。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成为别人,而不是成为自己。她看起来也像一个“无处安心的女孩”,面对不公拍案而起,抨击性别歧视,口无遮拦,不计后果。我爱科特妮·洛芙,她在洞穴乐队,我也在某种坑洞之中。
无数研究表明,少女有越来越高的风险患上躯体变形障碍(BDD),即对自己的身体有扭曲的看法,并执念于身体改造。我主要是不断试图隐藏自己的地中海人发色,也有很多女孩为了改变和控制自己的身形而陷入进食障碍。患有ADHD会提升青少年患躯体变形障碍和进食障碍(尤其是神经性贪食)的风险,又因为ADHD女孩往往善于掩饰,我们也很容易成为隐藏进食障碍的专家。
英国作家卡罗琳·克里亚多·佩雷斯在她的著作《看不见的女性》中谈到女孩的孤独症症状常被忽视:“新出现的证据表明,一些患有厌食症的女孩实际上可能患有孤独症,但由于厌食不是男性孤独症的典型症状,所以一直被忽视。”针对ADHD也有类似研究,但数量不多。由于女孩会表现出的症状更多样、更内化,这些症状可能也确实会导致并发性障碍,从而会掩盖她们正在承受的孤独症和/或ADHD。
ADHD、进食障碍和性别焦虑间也存在联系。2017年,土耳其研究人员发现,性别焦虑者最常见的共患诊断就是ADHD,这意味着ADHD人士比神经典型人士更有可能质疑自己的性别。2020年的另一项关于跨性别和性别多元群体的神经发育障碍和精神障碍率的研究表明,这些群体中ADHD和孤独症人士的比率高于顺性别者。
关于跨性别者和非常规性别者的ADHD研究并不多,但2018年的一份文献综述发现,缺乏社会支持的青少年性少数者更有可能“患抑郁、焦虑,酗酒或滥用药物,发生高危性行为,感到羞耻,以及低自尊”。这与许多关于神经发散青少年的研究不谋而合,虽然目前还没有针对青少年中既是神经发散者又是性少数者的研究,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群体会更脆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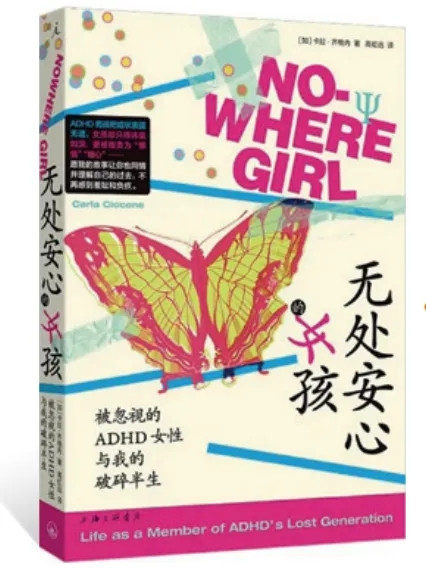
《无处安心的女孩——被忽视的ADHD女性与我的破碎半生》
[加]卡拉·齐格内 著
高虹远 译
上海三联书店
2025年11月
(本文摘自《无处安心的女孩——被忽视的ADHD女性与我的破碎半生》;编辑:许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