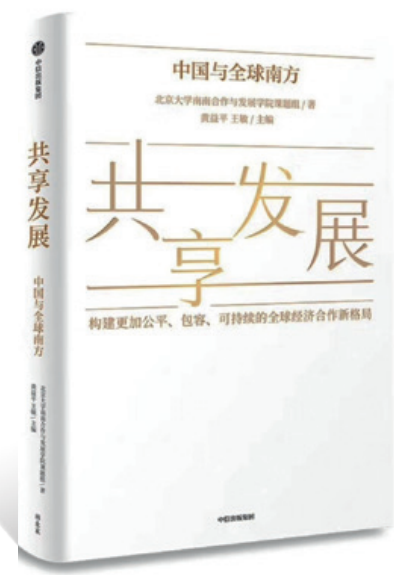
《共享发展》
黄益平 王敏 主编
中信出版集团
2025年10月
2025年7月17日,我与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下称“南南学院”)的几位同事抵达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市,与当地政商学各界展开交流与研讨。正好在同一天,坦桑尼亚总统萨米娅·苏卢胡·哈桑发布了《2050年愿景》(下称《愿景》),期望到2050年,坦桑尼亚的GDP(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亿美元,人均GDP达到7000美元,消除极端贫困,并成为非洲十大经济体之一。2024年坦桑尼亚的人均GDP为1268美元,这意味着在未来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人均名义GDP的年均增长率要达到6.8%,如果加上约3%的人口增长率,GDP的平均增速需接近10%。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规划。因为坦桑尼亚在2025年10月举行大选,不排除执政党在这个时间点发布《愿景》,部分是为了提振选情。《愿景》提出了一些战略支柱与产业政策,包括综合物流、能源革命、科技赋能、研发驱动、数字化转型,以及通过聚焦农业、旅游业、工业、建筑业、采矿业、蓝色经济、体育创意产业、金融服务、客户服务业等九大产业,实现就业创造与出口拉动的目标。但《愿景》并未提供具体的策略与路径,虽然政府表示将建立长期展望与五年计划双轨推进的方式。
如何成功推动经济发展、摆脱贫困、改善人民生活质量,是很多南方国家长期面对的难题。
自二战结束以来的80年间,学界与政界都做了很多努力。“发展经济学”形成的大背景,就是二战以后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诉求,国际组织也提出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2023年,联合国有193个成员国,其中36个是发达国家,157个是发展中国家。几十年来这个分组的变化不太大,说明无论是发展经济学学术理论还是“华盛顿共识”政策框架,在指导、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成效相对有限。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亚洲四小龙和中国等成功的亚洲经济体的政策却常常因为“过大”“过多”的政府作用而受到批评。
作为一个成功实现经济起飞的南方国家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能为全球南方发展贡献什么?
一方面,南方国家是否可以借鉴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政策?中国实行渐进式、双轨制改革策略,虽然看起来不太彻底,但4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是客观事实,也许中国的做法对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具有启示意义。另一方面,中国能如何促进全球南方的合作与发展?在国际经济秩序出现动荡、新的技术革命扑面而来的当下,中国能否发挥创新推动者与稳定维护者的作用,对于全球南方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华盛顿共识”可能已经成为过去时。一方面,“华盛顿共识”指导南方国家的改革与发展,成果不多。另一方面,包括美国在内的北方国家也已经放弃了这一共识的一些基本原则。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其原理是完全错误的,只是表明它的现实指导意义有限。
在“华盛顿共识”之后,也出现过不同的替代概念,比如乔舒亚·库珀·拉莫在2004年提出的“北京共识”,以及蒂姆·贝斯利、艾琳·布切利、安德烈斯·贝拉斯科等在2025年牵头提出的“伦敦共识”。
毫无疑问,最有影响力的当数以2001年诺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为首的专家在2008年提出的“后华盛顿共识”。
斯蒂格利茨认为,成功的发展战略不应只出自华盛顿,而更应该来自发展中国家;“一刀切”的策略注定不会成功;各个国家应该更多地以自己的判断,勇于尝试;相对平衡政府与市场的作用;GDP增长不应是唯一的衡量标准,同时也应关注分配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性。这些主张切中了“华盛顿共识”的要害,可惜的是,这些理念迄今尚未在南方国家形成实质性的正面影响。
中国等东亚经济体提供了南方国家快速实现经济起飞的成功案例,这些经验对于广大的南方国家具有更大的借鉴意义。仔细观察中国的政策实践,有两个方面的特点值得深入分析:一是从实际出发,制定适合国情的经济政策,不盲目追求理论最优;二是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虽然两者之间的分工可能因时、因地、因事进行调整。这两条意味着,决策的主动权掌握在本国人的手上,而不是由外部强加,更不是接受“一刀切”的方案。因此,政策决策既需要科学,更是一门社会艺术。
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什么作用?这是一个世纪话题。从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开始,经济学一向都重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配合。早在1848年,约翰·穆勒就提出,市场决定生产什么和怎么生产,政府则利用税收与转移支付解决市场失灵与分配问题。历史学家雅各布·索尔认为,经济学中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其实是近期才出现的现象,可能跟米尔顿·弗里德曼倡导的学术思想有关。同期,尤金·法马提出了金融领域的有效市场假说。
当时的大背景是二战以后,世界经济在美国的引领下逐步走向开放与融合,推动了全球范围的效率提升与经济繁荣。但越来越突出的不平等问题最终导致美国的经济政策出现了反转,尤其是在2017年特朗普第一次就任美国总统以后。效率与公平之间如何平衡,是经济学的世纪难题。美国的经历表明,即便是有效的市场,也无法很好地平衡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
在南方国家,政府与市场相结合可能更有必要,因为在大多数南方国家尚未形成成熟、有效的市场。至于政府具体应该做什么,最好是采取“务实”的态度。
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分工应该保持灵活、开放,重要的是看结果,看是否有利于实现稳健、快速、可持续的发展。比如在一些南方国家,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却没有形成任何劳动密集型产业。那就需要追问其背后的原因: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税收负担过重?营商环境不佳?劳动雇用成本过高?或其他?如果确定了瓶颈因素,政府就可以有针对性地缓解这些约束条件。
基于这样的考虑,也许有必要就什么是适合南方国家经济发展的政策框架展开广泛的探讨,充分吸取在过去几十年取得经济成功的南方国家的经验教训,进而形成“全球南方共识”。讨论这个共识的目的,并不是要替代之前的共识,更不是要提出一揽子的政策措施,而是探索适合应用于南方国家经济政策决策的一些基本原则。
具体的内容,需要关注全球南方发展的专家学者共同讨论、推究,但下面几个方向可以作为讨论的起点与基础:
一是追求由市场决定要素和产品的配置与定价。在很多南方国家,更好地完善市场机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是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发展的必要步骤。
二是政府采取务实的改革政策,完善市场体系。但建立、完善机制与制度,“一放了之”不见得能达成目的,而需要制定、实施符合国情、满足可行性条件的措施,持续推进。
三是政府与市场结合,克服市场失灵。除了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政府还需要弥补市场不足。但克服市场失灵,不能演变成替代市场功能。比如政府制定产业政策,目的是解决外部性问题,支持企业创新、产业升级,因此,产业政策不应破坏妨碍竞争,更不应该由政府“选择胜出者”,还要预先设定明确的退出机制。
四是增长至关重要,但就业、平等、环保、稳定与安全同样很关键。对于南方国家来说,经济增长是首要目标。经验也表明,实现增长是减少贫困的最有效手段。与此同时,经济韧性也很重要,这样经济增长才能长期持续,也才能更好地达成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不断增长的需要的目的。
五是稳健开放贸易与投资,加强南南合作。成功的东亚经济体的经验表明,参与国际劳动分工是南方国家实现快速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但开放也可能会带来一定的风险,所以需要采取稳健的策略。
现在一些北方国家的对外经贸政策出现了逆转,南方国家如何坚持开放的方向,但又不致遭遇严重的外部冲击,是一个新的课题。南方国家如何促进全球经济体系的开放以及相互之间如何加强合作,这些话题都值得深入探讨。
上述五条只是我个人的一些非常不成熟的看法。推动“全球南方共识”的形成,需要与南方国家的各界展开广泛的研讨。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对经济政策的立场也不一样。但借鉴一些成功的南方国家的经验,提出一些适合南方国家国情的基本共识,从而指导南方国家的改革与发展政策,于全球南方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日益增大的今天,将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对于像坦桑尼亚这样力图振兴经济的南方国家,“全球南方共识”可以提供有益的政策原则与框架。
如果能够达成“全球南方共识”,也不宜由像IMF这样的国际组织去推行。因为这样的共识内生于南方国家,像“金砖国家”(BRICS)这样的全球南方组织可以广泛地就共识的内容展开讨论,甚至搭建交流与讨论的平台,但具体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的主导权一定要留给南方国家。
“全球南方共识”是根据一部分南方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大多数南方国家的实际情况形成的,其最重要的特点是务实,这意味着经济政策既要遵循一些共同的原则,实际工作中也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同时还要与时俱进。
(本文摘自《共享发展》;编辑:许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