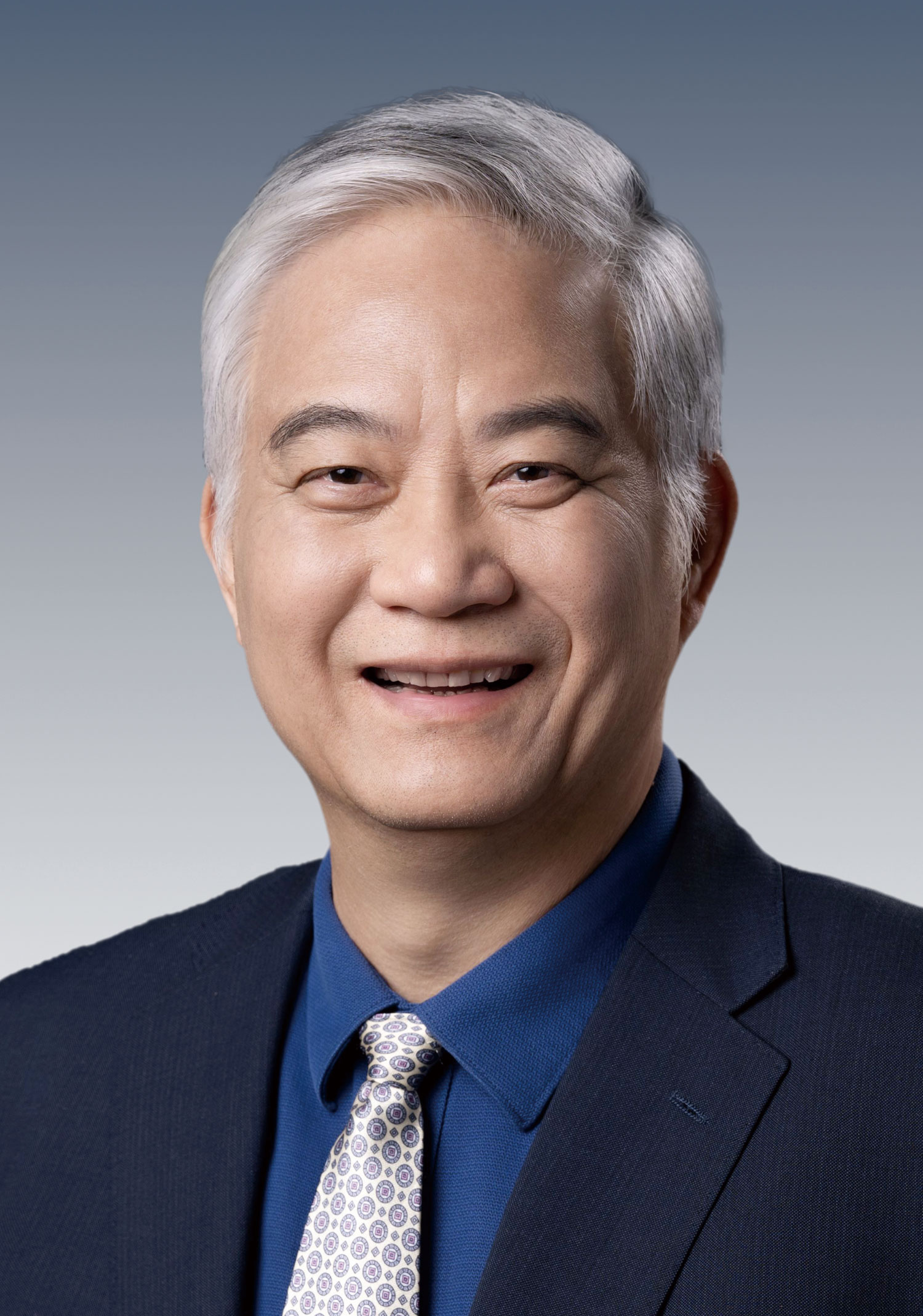
我们的文化有着实用主义的基因。谈及科技,我们往往重“技”轻“科”。中国科技已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若想实现从“跟跑者”向“领跑者”转身,还须挣脱文化层面的羁绊,打造更为宽松包容的基础科研生态。唯此,中国科研方能孕育出更多改变世界的原创性成果。
中国科技原创乏力的根源
中国科技的飞跃有目共睹。去年10月,《自然》刊发专题文章,对各国科技发展态势展开对比。数据显示,中国年度研发经费总量已突破8000亿美元,逼近美国的9000多亿美元水平;高被引论文总量更是超越美国,在材料、化学、工程、计算机、环境、物理等领域表现尤为突出。然而“短板”亦不容忽视。如在生物和生物化学领域,美国高引论文占比近50%,中国仅为约30%。最核心的警示在于,中国原创性成果相对匮乏。以AI领域为例,中国虽跟进迅速,却往往未能触及底层逻辑的革新。我们擅长“从1到10”的优化升级、“从10到100”的规模扩张,但在“从0到1”的原创突破上步履维艰。
原创成果的稀缺,根源在于文化与价值层面的桎梏。中国社会推崇实用主义,导致科研工作往往聚焦于短期成果与实际应用,却忽视了基础研究与原创探索的长远价值。教育领域同样弥漫着实用主义乃至功利主义的气息。学生选择专业时,更多考量的是就业前景与收入水平。这种选择于个人而言无可厚非,但社会对“有用性”的偏执追求,使得甘愿投身基础研究的人才少之又少。重塑文化土壤、培育大师辈出的环境,仍是一项任重道远的使命。
一个社会的价值崇尚,决定着一个民族的未来走向。16世纪以来,欧洲“有闲阶层”乐于科学探索,正是这个阶段东西方文明发展的代际差距显现。中国已具备坚实的经济基础,应为顶尖科学家提供充足的经费支持与自由的探索空间,让他们能心无旁骛地深耕基础研究。唯有科学家们能从容探索看似“无用”的真理时,中国才能真正跻身世界科技之巅。
科研管理的困局:信任缺失与机制僵化
原创成果的培育,既需文化沃土,更需制度保障。当前中国科研管理中,过度干预与繁琐审批的问题较为突出,妨碍了科学家潜心研究。
容错机制的缺位,亦是创新路上的绊脚石。基础研究本就是“大概率失败、小概率成功”。若项目失败就要追责,谁还敢触碰风险大的“未知”领域?反观国外,不少大企业向大学捐赠资金时已做好“打水漂”的准备,这既源于长期主义的视野,也得益于科研免税政策的激励。相比之下,中国科研管理亟待从“防错”转向“促创”,在考核与容错间找到平衡点。
人才政策的问题也不容忽视。海外优青要求申请者必须在境外从事三年博士后研究,实际上真正优秀的年轻人大多只会做两年博士后。双重国籍的限制,将不少海外优秀华人学者及其子女拒之门外。印度通过“海外公民卡”吸引全球印裔人才的做法,或许值得中国借鉴。顶尖人才的流动不应被身份标签束缚。
城市教育的突破:以深圳为样本的思考
城市是科技生长的土壤,而大学则是土壤中的“根系”。深圳的人口规模远超香港,GDP也已实现超越。深圳重视教育与科研,高校数量近年来快速增加,但与香港的大学密度相比,深圳的“智力引擎”仍显薄弱。纵观全球,优秀城市(名城)无不拥有顶尖大学(名校)。深圳要保持领先优势,仍需持续加大教育投入。
补短板的路径并非唯一,教育破局的关键在于释放民间活力。美国的知名高校多为私立大学,而中国民间资本办学仍受较多限制,不过目前已有积极探索,如西湖大学、福耀科技大学等高校的建立便是有益的尝试。政府应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科研与教育事业,尤其要吸引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投入。这不仅能为政府减负,更能让教育生态呈现百花齐放的态势,进而激发竞争与创新活力。


